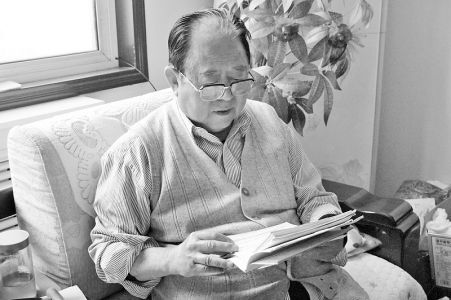日期:[2015年05月06日]
-- 牡丹晚报 --
版次:[A11]
抗美援朝战场上,他躲过了六架敌机扫射
□牡丹晚报记者 武 霈
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5周年。5月3日,在巨野县田桥镇王楼村,牡丹晚报记者慕名采访了81岁的老兵王炳慈。作为65年前第一批跨过鸭绿江、奔赴朝鲜战场的热血战士,那壮怀激烈的岁月是他毕生难以磨灭的印记,沁入血液,融入骨髓。即使到了65年后的今天,面对牡丹晚报记者的采访,听到“抗美援朝”这四个字,王炳慈的双眸依然闪耀着光芒。
“渡过鸭绿江的第六天,我便遇到了麻烦,敌军六架飞机对我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的追击、扫射,这是一次最接近死亡的逃生。”回想起当日的情景,王炳慈的表情异常复杂,恐惧、愤怒、幸运兼而有之,“每次回想起这段经历,我全身的汗毛都会立起来了,浑身冰凉冰凉的。”
他16岁上前线,成为首批志愿军
5月3日上午,当牡丹晚报记者走进王炳慈家中时,戴着一副老花镜的他正在整理记录抗美援朝战争记忆。尽管已年逾八旬,老人家依然面色红润、精神矍铄、腰板硬朗,且热情、随和。他笑着对记者说:“年纪越大,对以前的回忆就越是深刻,很高兴你能听我讲述当年的故事。也别正式采访了,我就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小兵,咱就拉拉呱吧。”
1949年参加解放军的王炳慈属于三野九兵团第二十军,奉命驻守在上海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,年仅16岁的他成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、走上抗美援朝最前线的志愿军。“当时我只有16岁,应该是我们整个营队里最年轻的士兵。我当时属于机炮连,负责运送、发射步兵中的重武器:迫击炮。”王炳慈回忆道,“我1950年11月6日渡江,1952年10月2日返程,在战场上度过了将近两年。”
两年间,王炳慈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,“一场阻击战就要打两三个月,每次战役都要打很多场,连续性作战,先不说缺吃少穿、天气严寒,单单是连续几个月的精神高度集中,就能让人崩溃。”王炳慈说。
为掩护营队,他遭遇6架敌机扫射
上战场前,尽管王炳慈早就对残酷的战役做足了心理准备,但与死神的对话仍然给他上了一课。“过江后的第六天,我遇到了第一次麻烦。”虽然语气平静,但王炳慈复杂的表情却告诉牡丹晚报记者,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。
“当时我和两位战友在一所朝鲜农家大院里推磨、准备晚饭。约八点钟左右,我听到飞机的引擎声,便警惕地探出头观察,好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,只是象征性地盘旋了一下,然后飞了过去。可我们刚松了一口气,哒哒哒……敌机却开始对整个大院进行扫射了。”王炳慈说,“不过,当时敌人并不知道有人,只是胡乱扫射一通,我们连忙隐藏。”
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:这时,与王炳慈一起躲在磨盘后的一位战友负了伤。“在我旁边的陈副班长被射中了,膝盖上有一个三角口子,鲜血直流。我和另外一位战友赶紧为他包扎,可依然血流不止。这时,院子里运输重型武器的骡子受惊嘶叫,我们暴露了,必须转移。”王炳慈让另一位战友背着陈副班长先行离开,自己收拾救济包和粮袋殿后。
当王炳慈走出农家大院的时候,敌军两架飞机也锁定了目标,对他进行扫射。王炳慈连忙朝山上的防空洞奔去。“砰砰”,此时山上鸣起枪响,“我如果往防空洞跑,整个营队都会暴露。”考虑到这一点,王炳慈没有犹豫,迅速朝反方向奔去,敌军两架飞机紧随其后。
“当时两架飞机一直俯冲、扫射,每当飞机低飞的时候,我就趴在地上打滚,可一抬头,飞机就在眼前,那种感觉几近绝望。”忆及当时的场景,王炳慈至今仍心有余悸。幸运的是,王炳慈顺利逃到了对面的一座山头上,但敌机并没有撤离。
令人恐惧的是,此时又飞来了4架飞机,轮番对这个小山头进行轰炸。“咚,一颗炸弹落在我附近,瞬间,我啥也看不到了,耳朵嗡的一下,啥也听不到了。过了好一阵子,我逐渐清醒过来,摸了摸胳膊、腿,都还在,看样子还没死。求生,一定要活着—这是当时我唯一的想法。”王炳慈此时的声音已经颤抖了,“在那个山头上,我看见缝隙就钻,不敢出来。六架飞机轰炸了3个多小时,最后又返回,在农家大院丢了一颗汽油弹,引燃了所有的房屋才离开了。”
回到营部后,战友们围拢过来,关切地说:“好险啊,我们以为你不行了,没想到你还活着!”心有余悸的王炳慈不知该如何回答,只是笑了笑:“我去报到了,可阎王爷不收,我又回来了。”
噙满双眼的泪水将老人的思绪从65年前拉了回来,王炳慈用纸巾抹了抹眼睛,告诉牡丹晚报记者:“我就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个普通小兵,让我活着返回家乡的不仅仅是幸运,还有对国对家的信念,这种信念是每一位上战场的勇士都必须具备的。”
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5周年。5月3日,在巨野县田桥镇王楼村,牡丹晚报记者慕名采访了81岁的老兵王炳慈。作为65年前第一批跨过鸭绿江、奔赴朝鲜战场的热血战士,那壮怀激烈的岁月是他毕生难以磨灭的印记,沁入血液,融入骨髓。即使到了65年后的今天,面对牡丹晚报记者的采访,听到“抗美援朝”这四个字,王炳慈的双眸依然闪耀着光芒。
“渡过鸭绿江的第六天,我便遇到了麻烦,敌军六架飞机对我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的追击、扫射,这是一次最接近死亡的逃生。”回想起当日的情景,王炳慈的表情异常复杂,恐惧、愤怒、幸运兼而有之,“每次回想起这段经历,我全身的汗毛都会立起来了,浑身冰凉冰凉的。”
他16岁上前线,成为首批志愿军
5月3日上午,当牡丹晚报记者走进王炳慈家中时,戴着一副老花镜的他正在整理记录抗美援朝战争记忆。尽管已年逾八旬,老人家依然面色红润、精神矍铄、腰板硬朗,且热情、随和。他笑着对记者说:“年纪越大,对以前的回忆就越是深刻,很高兴你能听我讲述当年的故事。也别正式采访了,我就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小兵,咱就拉拉呱吧。”
1949年参加解放军的王炳慈属于三野九兵团第二十军,奉命驻守在上海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,年仅16岁的他成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、走上抗美援朝最前线的志愿军。“当时我只有16岁,应该是我们整个营队里最年轻的士兵。我当时属于机炮连,负责运送、发射步兵中的重武器:迫击炮。”王炳慈回忆道,“我1950年11月6日渡江,1952年10月2日返程,在战场上度过了将近两年。”
两年间,王炳慈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,“一场阻击战就要打两三个月,每次战役都要打很多场,连续性作战,先不说缺吃少穿、天气严寒,单单是连续几个月的精神高度集中,就能让人崩溃。”王炳慈说。
为掩护营队,他遭遇6架敌机扫射
上战场前,尽管王炳慈早就对残酷的战役做足了心理准备,但与死神的对话仍然给他上了一课。“过江后的第六天,我遇到了第一次麻烦。”虽然语气平静,但王炳慈复杂的表情却告诉牡丹晚报记者,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。
“当时我和两位战友在一所朝鲜农家大院里推磨、准备晚饭。约八点钟左右,我听到飞机的引擎声,便警惕地探出头观察,好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,只是象征性地盘旋了一下,然后飞了过去。可我们刚松了一口气,哒哒哒……敌机却开始对整个大院进行扫射了。”王炳慈说,“不过,当时敌人并不知道有人,只是胡乱扫射一通,我们连忙隐藏。”
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:这时,与王炳慈一起躲在磨盘后的一位战友负了伤。“在我旁边的陈副班长被射中了,膝盖上有一个三角口子,鲜血直流。我和另外一位战友赶紧为他包扎,可依然血流不止。这时,院子里运输重型武器的骡子受惊嘶叫,我们暴露了,必须转移。”王炳慈让另一位战友背着陈副班长先行离开,自己收拾救济包和粮袋殿后。
当王炳慈走出农家大院的时候,敌军两架飞机也锁定了目标,对他进行扫射。王炳慈连忙朝山上的防空洞奔去。“砰砰”,此时山上鸣起枪响,“我如果往防空洞跑,整个营队都会暴露。”考虑到这一点,王炳慈没有犹豫,迅速朝反方向奔去,敌军两架飞机紧随其后。
“当时两架飞机一直俯冲、扫射,每当飞机低飞的时候,我就趴在地上打滚,可一抬头,飞机就在眼前,那种感觉几近绝望。”忆及当时的场景,王炳慈至今仍心有余悸。幸运的是,王炳慈顺利逃到了对面的一座山头上,但敌机并没有撤离。
令人恐惧的是,此时又飞来了4架飞机,轮番对这个小山头进行轰炸。“咚,一颗炸弹落在我附近,瞬间,我啥也看不到了,耳朵嗡的一下,啥也听不到了。过了好一阵子,我逐渐清醒过来,摸了摸胳膊、腿,都还在,看样子还没死。求生,一定要活着—这是当时我唯一的想法。”王炳慈此时的声音已经颤抖了,“在那个山头上,我看见缝隙就钻,不敢出来。六架飞机轰炸了3个多小时,最后又返回,在农家大院丢了一颗汽油弹,引燃了所有的房屋才离开了。”
回到营部后,战友们围拢过来,关切地说:“好险啊,我们以为你不行了,没想到你还活着!”心有余悸的王炳慈不知该如何回答,只是笑了笑:“我去报到了,可阎王爷不收,我又回来了。”
噙满双眼的泪水将老人的思绪从65年前拉了回来,王炳慈用纸巾抹了抹眼睛,告诉牡丹晚报记者:“我就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个普通小兵,让我活着返回家乡的不仅仅是幸运,还有对国对家的信念,这种信念是每一位上战场的勇士都必须具备的。”